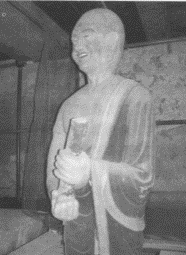2025年世界讀書日“藝術與閱讀”系列活動 | 書香敦煌 人神共讀——敦煌莫高窟藝術寶庫中的讀書圖展講(一)
來源:發(fā)布時間:2025-05-04 作者:點擊: 次

點擊上方“弘雅書房”→點擊右上角“...”→設為★
設置星標后,再也不會錯過每一期的精彩文章啦!

敦煌莫高窟是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,被譽為“東方藝術明珠”。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堅時期,據(jù)唐朝《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》記載,前秦建元二年(366年),僧人樂僔路經此地,忽見金光閃耀,如現(xiàn)萬佛,便在巖壁上開鑿第一個洞窟,居留修行。此后法良和尚等接續(xù)在此建窟,稱為“漠高窟”,意為“沙漠高處之窟”。后世因“漠”與“莫”通用,便改稱為“莫高窟”。另有一種說法為:佛家有言,修建佛洞功德無量,“莫”者,不可能、沒有也,莫高窟的意思,就是說沒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功德了[1]。
北魏、西魏和北周時,統(tǒng)治者崇信佛教,石窟發(fā)展較快。隋唐時期,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,莫高窟達至最盛,在武則天時有洞窟千余個,故又稱“千佛洞”。安史之亂后,敦煌先后由吐蕃和歸義軍占領,但開窟造像活動未受太大影響。北宋、西夏和元代,莫高窟漸趨衰落,以重修前朝窟室為主,新建極少。元代以后敦煌停止開窟,逐漸沒落。明嘉靖七年(1528年)封閉嘉峪關,敦煌淪為邊塞游牧之地,愈加荒涼。清代,晚清政府腐敗無能、西方列強侵略中國,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、日人橘瑞超、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險家接踵而至敦煌,以非法手段,從道士王圓箓手中掠取大量文物,分藏于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國的公私收藏機構,僅余少部分保存于國內,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。
基于以上發(fā)展歷程,可見敦煌莫高窟最大宗最輝煌的作品出自唐及五代,是唐及五代文化藝術的杰出代表,考察唐及五代的讀書圖,不能不重點關注敦煌莫高窟遺存的藝術作品。莫高窟現(xiàn)存4.5萬平方米的壁畫,還有大量塑像和紙帛畫,包羅萬象,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,世人矚目。百余年來,對于莫高窟的藝術作品,學者們做了大量研究,但是對其中存在多少幅讀書圖?這些讀書圖揭示的中古時期人們的讀書場景是什么樣的?佛教對于書籍和閱讀秉持什么樣的態(tài)度?這些讀書圖對書史、閱讀史、文化史研究有何價值?諸如此類的問題,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。下面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析。
1、 莫高窟藝術寶庫中的讀書圖概況
所謂讀書圖,指的是人物和書籍處于同一畫面,人物做出將要閱讀、正在閱讀或剛剛讀畢之狀的圖畫[2]。但在初步調研中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照此定義進行檢覽,符合條件的讀書圖少之又少,于是將讀書圖的外延適當作了擴展,把出現(xiàn)圖書的畫面都視為讀書圖。
為盡可能全面獲取敦煌莫高窟遺存的讀書圖,我們采取多種途徑:一是翻檢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與敦煌莫高窟藝術作品有關的圖書。二是以“閱讀”“讀書”“經卷”“聽經”“誦經”“寫經”“造經”“捧經”“學郎”“學童”“文士”等和讀書相關的詞匯為關鍵詞,先對敦煌研究院網站的“數(shù)字敦煌”進行檢索,然后檢索兩個藝術品數(shù)據(jù)庫:Airlib世界藝術鑒賞庫[3]和雅昌藝術教育課堂[4]。三是通過百度、谷歌等搜索引擎進行全網搜索。四是仔細瀏覽甘肅省特別是敦煌市的圖書館、文物部門、文旅部門等單位的微信公眾號和網站,從中尋找相關圖片和線索。五是動員師友廣泛收集。故而多數(shù)圖片有多個來源,文中選用最清晰的那幅。
通過各種途徑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22幅有代表性的讀書圖,它們相對契合讀書圖的定義,是敦煌莫高窟讀書圖的主體及絕大部分,但不是其全部。因為莫高窟遺存圖像的畫面元素十分復雜,包羅萬象,散落英法俄日等多個國家,搜羅殆盡十分困難。有些類型的與讀書有關的圖像,如行腳僧圖,已有學者作了系統(tǒng)梳理,找到了20幅,寫了圖像志[5]。考慮到此類圖畫數(shù)量較多,且多數(shù)屬于外圍性質的讀書圖,便只選取其中書香氣息最為濃郁、釋放文獻信息最多的兩幅。與行腳僧圖類似的,還有8幅地府十王圖、10幅經架圖可作專題研究,限于篇幅,本文也僅選取最具典型性的加以探析。選取的22幅讀書圖還包括塑像,因為塑像可視之為立體的圖畫。
下面我們依照圖像中用書人身份在佛教階層中由低到高的順序,列表簡介供養(yǎng)人讀書、比丘讀書、行腳僧讀書、善惡童子之書、星神讀書、尊者讀書、菩薩讀書、彌勒用書的圖像,見表1。其中從數(shù)據(jù)庫中檢索到的圖像,可獲取較多的著錄信息,故在“相關信息”一欄揭示較詳,而從其他途徑得到的圖像,作品的材質、尺寸等信息不詳,揭示相對簡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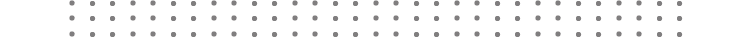
表1 敦煌莫高窟藝術寶庫中的讀書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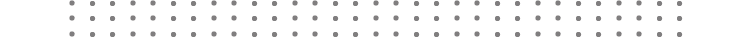
2、 莫高窟藝術寶庫中的讀書圖探析
敦煌莫高窟讀書圖包含豐富的宗教故事、雋永的人生哲理、良善的社會倫理、獨特的史料價值等,下面我們按照用書人身份在佛教中的階層,由低到高,逐類對這些讀書圖試作探析。
體罰學郎圖反映的是敦煌地區(qū)在學處或僧寺求學的普通青少年的讀書求學情況。
雖然敦煌壁畫的主旨是宣傳佛教,但因其畫匠多出自當?shù)兀厝灰獜漠數(shù)氐氖浪咨钪屑橙§`感,畫中便不乏與當?shù)亟逃芮邢嚓P的元素。例如,創(chuàng)作于五代的莫高窟468窟北壁《藥師經變》,生動刻畫了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》中的情節(jié)。所謂經變,指的是描繪佛經內容或佛傳故事的圖畫,又稱變相、佛經變相。《藥師經變》中有個局部反映了當時學校教育活動的狀況,畫匠以1座庭院、6個人物(2位學官、4名學郎)展示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》中的“學處”場景,見圖1。

圖1 莫高窟468窟北壁《藥師經變》中的體罰學郎情景
經中三次提到學處,學處指的是聽經學法的地方,第一次是:“復次,曼殊室利,若諸有情,雖于如來受諸學處,而破尸羅。”[6]104第二次是:“如來法中,受持學處,無有毀犯,正見多聞,解甚深義,離增上慢,不謗正法,不為魔伴,漸次修行諸菩薩行,速得圓滿。”[6]104第三次是:“有能受持八分齋戒,或經一年,或復三月,受持學處,以此善根,愿生西方極樂世界,無量壽佛所,聽聞正法……”[6]180第一次強調要用心投入、遵規(guī)守紀,不可破戒,第二次講要態(tài)度端正、循序漸進,第三次指出要持之有恒。
如果完全依照經文,畫家應該塑造一個理性刻苦的好學生的形象,與體罰無關。但是經變畫就是改編畫,允許畫家進行接地氣的生動演繹,讓老百姓喜聞樂見,對佛教產生好奇乃至崇信,于是畫家反向思維,大膽設計了一個老師正在體罰學生的情節(jié)。畫中,一位學官(居左者)端坐殿堂,橫眉冷對,似在“督戰(zhàn)”,另一位學官(居右者)表情嚴厲、手執(zhí)教鞭,正在抽打一名高大壯實的學生,而且勒令學生將袍腳、袖口都高高挽起,裸露腿部、手臂。看來已經體罰了一會,學生腿上臂上都留下了多道血痕。學生行為上很順從,手挽袍腳讓老師打,但精神上不服氣,以倔強的眼神瞪著老師。學處教室里的其他三位學郎,兩位已打開書卷,一位正在打開,此刻都把眼神從書本上挪開,以驚愕、同情的眼神看著同學被體罰。從后排靠右學郎握持的那本未打開的書的樣式看,其形制明顯是卷軸。
有意思的是,與“體罰學郎圖”情境相似的另一幅學堂圖出自晚唐第12窟主室東壁,見圖2。該窟建于晚唐咸通十年(869)前,五代重修。因主室東壁門上方有“窟主沙州釋門都法律和尚金光明寺僧索義”墨書題記,所以又被稱作“索法律窟”。該窟主室繪經變十幅,而表現(xiàn)上圖中“學處”的《維摩詰經變》繪于東壁門北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方便品第二,講的是維摩詰居士的方便教化行持,也就是菩薩入世教導眾生的無量方便法門。經變中跟教學或學處有關的演繹應該出自此處。
兩幅不同的壁畫演繹不同內容的佛經,兩個學處在空間設計上居然如出一轍,主體都是一個庭院,院中有一個廡殿式中堂,兩邊帶有廂房,一側可見的廂房內有三名學生正在讀書,條件簡陋,課桌是支起的木板,坐的是一方形土墩,課本是手抄的紙卷,展開平鋪桌上,庭院里有一名學生、兩名老師,可見這種建筑樣式和這種師生規(guī)模與配比是當時學堂的常見配置或標準配置[7]。
截然不同的是,《藥師經變》意在刻畫“師之嚴教”,《維摩詰經變》旨在強調“尊師重教”,畫了一名學生俯身九十度,手捧茶水,禮敬師者。兩位師者,居中者為老師,側坐者為維摩居士,表現(xiàn)的即《維摩詰所說經》“方便品第二”的“入諸學堂誘開童蒙”[8],見圖4。這兩幅關于學處的壁畫,從罰與敬、嚴與溫兩個角度再現(xiàn)了中古時期敦煌一帶學堂教育的景象,畫面中教師嚴謹負責、學郎尊敬師長的精神,對于當今如何正確地定義、定位教師不無啟示意義,對于扭轉當今教育的某些不良現(xiàn)狀,樹立正確的教書育人觀、弘揚尊師重教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不無裨益。

圖2 晚唐第12窟主室東壁《維摩詰經變》中的學處
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的彌勒經變壁畫有兩處畫到讀書,反映的是供養(yǎng)人或信徒、居士的讀書狀況,主要是聽經、寫經和誦經。
一處是在綠樹蔭下,有一位戴著唐代式樣的結巾長腳羅幞頭、身穿褐色圓領袍的文士樣貌的信徒,雙手合十跪在一位僧人面前,正在聽僧人講經說法。僧人坐在矮榻上,手展卷軸,正在認真誦讀,見圖3。

圖3 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《彌勒經變》中的聽經
另一處是在小樹林中,一位同樣裝扮的信徒坐在矮榻上,正在伏案執(zhí)筆,準備抄寫佛經,見圖4。這名信徒手按的物體,顯然不是裝裱好的空白卷軸,一是因為卷子中間明顯平坦,非圓柱狀;二是因為卷端未見突出的木軸;三是因為卷軸都是左右展開,此物是上下展開,如此寫經不合情理。他手按的是一個白色的枕狀物,兩頭圓形,中間似有崩弦,好像是一個兼有鎮(zhèn)紙和尺子功能的墨斗一樣的工具,這位信徒正在沿著崩弦為白紙描畫邊線和界線,為抄寫佛經作準備工作。

圖4 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《彌勒經變》中的寫經
關于這兩位信徒究竟是在做什么,權威的說明莫過于畫上的榜題和創(chuàng)作依據(jù)的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》。可惜的是,因年代久遠,榜題上的字跡已風化消失。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》與這兩處畫面最相關的內容是:“是諸人等,或以讀誦分別決定修妒路、毗尼、阿毗曇藏,修諸功德,來至我所。”[9]修妒路、毗尼、阿毗曇藏分別指經藏、律藏、論藏,大致對應于佛祖教義、戒律、佛祖教義詮釋三類佛教文獻。全句的含義是:各位信徒,你們也可以通過自行選擇讀誦經藏、律藏或論藏,修煉功德,超度升天,來到我處。
對照原文,可知畫家在創(chuàng)作中并未機械照搬原文,而是有所創(chuàng)新。原文是信仰者讀誦經文,畫家處理成了聽僧侶講經和自己寫經兩個場景。為了呈現(xiàn)信徒的虔誠程度,畫家以雅潔林地表達信徒對優(yōu)美聽寫環(huán)境的精心選擇,以穿戴嚴整表達信徒認真的聽寫態(tài)度,以跪坐恭聽和端坐細描表達信徒莊嚴的聽寫舉止,畫面雖簡卻講究細節(jié),耐人尋味,可謂精心構圖,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
畫家還采用分形手法,從兩位信徒身旁,各升起一條線,線條漸粗,化成彩云,云頭托起一人,就是信徒自己,表示這兩位信徒已經通過聽經和抄經得度升天了。
信徒也叫供養(yǎng)人,所謂供養(yǎng)人,就是以燃燈、獻花、讀誦、布施、香供、上食、開窟、起塔、造像等方式表達虔誠,以求得道升天的信徒。鳩摩羅什翻譯的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》許諾:在彌勒下生的世界,堅持修行、供養(yǎng)的人一定會遇見彌勒,通過聆聽彌勒的三次法會之一而得度超生[10]。
這幅壁畫從聽經寫經可以得道成佛的角度宣揚讀書,盡管是基于宗教目的,但對于觀賞壁畫的所有民眾而言,都有激勵讀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。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正是紙張漸趨普及,紙質卷子書代替簡帛書的階段,當時社會上出現(xiàn)一大批寫經生,如南朝劉宋的陶貞寶、南朝陳代的徐孝克等都是著名的寫經生[11]。此幅壁畫形象地揭示了當時的書籍形制、抄寫方式、寫經生樣貌,是生動的證史素材。
供養(yǎng)人寫經誦經圖還見于莫高窟第321窟主室南壁上的《十輪經變》,因此畫上方畫的是各種寶物如雨般紛紛墜落,所以又稱《寶雨經變》,這是莫高窟不多見的詳細宣傳地藏菩薩信仰的壁畫。壁畫東側中部集中展示供養(yǎng)諸佛、修積功德的方式,包括齋僧、燃燈、造房、治病、寫經、誦經、建塔等。關于寫經、誦經的部分,畫的是在一處沒有前墻的房屋中,一位黑衣人面西,正在寫經,一位青衣人面南,正在雙手捧經誦讀,兩位都頭戴卡其色尖頂軟帽,有些中亞人的特征,見圖5。

圖5 莫高窟第321窟主室南壁《十輪經變》中的寫經、誦經圖